尽管知识细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但是学科的划分却是古已有之。中世纪晚期由于各种壁垒的存在,学术的发展到了一个停滞的边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等多重因素,人们原有的宇宙观受到巨大冲击,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求知的领域从神圣世界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消融了各种隔离墙,在原本壁垒森严的不同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局面。“全才”的大量涌现与此有着内在关系,他们突破学科边界,拓展知识的范围,以创新而不是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志趣,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大发展。
达芬奇设计的水车手稿
“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
自古希腊以来,“智慧”就被视为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程度的知识,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崇高理想。柏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的理念的沉思,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对事物第一动因的知识,奥古斯丁称之为对不可见的无穷宝库的沉思。到中世纪后期,神学使人类脱离自然,人被固定在原罪上,只能在孤独的修炼中放弃感觉和一切有形的东西,摆脱尘世和人生的一切关系;哲学则成为了一种关于古典秩序的神学,这种秩序本身永恒不变,十分完善,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这个时期最高形式的智慧是一种沉思性美德,最为人所崇尚的生活是一种宗教性的沉思生活,如阿奎那通常把智慧局限在关于精神存在的知识和对上帝的沉思的范围之内,而在《神曲》中只有贝雅特丽齐可以被恰如其分地与智慧联系在一起,是她引导诗人走向沉思上帝的终极快乐。
在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晚期迈向早期现代的过程中,人们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崇尚沉思生活开始转向投身行动生活。这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对人自身的发现等,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遵循一种僵化的模式事先完全设计好的,而是可以通过人来改变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塑造。人关于宇宙的观念变得无限和开放,新的哲学从人的自由、意志和活力方面对人做出解释,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忏悔和自责中耗费一生,而应当去过一种拥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公开质疑沉思生活的优越性,想象另一种智慧的可能性:它是伦理的而非形而上的,是行动的而非沉思的。智慧被赋予了世俗含义,既可以属于修道院和大学,也可以属于市井社会;德行比关于真理的知识更重要,行动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智慧以具体的方式变得世俗化,带上了一种比以往更实用的色彩,人类事务开始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多位人文主义者对智慧的认识渐进性地呈现出上述变化。彼得拉克(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在作品中很少讨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或者系统性的神学,他崇尚的智慧从关于基督教原理的知识类型开始转向了伦理范畴。他的早期继承者萨卢塔提(ColuccioSalutati,1331—1406)比他更明确地提出:“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行动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比沉思生活更可取。”他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最好把自己限制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基本责任,有智慧的人理应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萨卢塔提之后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LeonardoBruni,1370—1444)重构了关于智慧的思想,明确表示厌恶那些对群体毫无贡献的沉思者。他还在书中引用西塞罗说过的一番话:就像马为了奔跑而生,牛为了犁地而生,狗为了气味的踪迹而生一样,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为了两件事而生,这就是知和行。
智慧内涵的变化使得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崇尚逐渐让位于世俗世界中的行动生活,这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艺术在西方语言里包含了技术的成分。达芬奇不仅以艺术文明,更以各种科学发明傲立文艺复兴时期。
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
伴随智慧内涵的世俗化及行动生活重要性的提升,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世界。新的宇宙观推倒了所有的隔离墙,理性和信仰、艺术和科学、理论和实践等之间的壁垒被渐次移除。首先,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中世纪学者虽然貌似对各种古典思想兼收并蓄,但却坚定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划出界限,相关学科的关系井然有序,各自的范围固定不变,彼此之间壁垒森严。1460年前后,费奇诺(MarsilioFicino,1433—1499)在佛罗伦萨发起了一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它如燎原之火,势不可当,冲破了原有的种种藩篱。新柏拉图主义者尝试融合古典和中世纪这两种彼此不同的文化世界,不仅打破了哲学、宗教和魔术之间的隔离墙,而且消融了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
其次,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在一个彼此交融的前沿共同发展。这个时代艺术的繁荣至少应当部分归功于科学,而对于科学的进步,艺术同样功不可没。譬如,画家阿尔伯特在关于形式的原则中综合了艺术和科学两方面的理论,希望把人物的心灵活动展现在肢体动作上,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家必须全面掌握人体的各个细微之处,如果能画好这些部位,他就能给观者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在阿尔伯特之后,达·芬奇集艺术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于一体,他让解剖服务于艺术,又让艺术服务于解剖,使解剖符合人体器官的形式及功能,因对象的年龄、性别和生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解剖学的发展。
再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被冲破。在中世纪,两者之间缺少互动,工程师和手工艺人的创造发明难以进入“自然哲学家”的视野,反之亦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推演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12世纪时曾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但是直到16世纪才有人意识到,让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塔楼上坠落,便可以对此进行检验。中世纪即便是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理论和实践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比如,中世纪的天文观测和计算都精确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猜测也极具洞察力,可是没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沟通渠道。
学科之间因“隔离墙”的消除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和渗透的局面。这是一种各学科之间的完满融合,是一种创造性的和谐共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划分初露端倪时,方告结束。
100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局部
“全才”的涌现和学术大发展
随着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全才”(l’uomouniversale)大量涌现。所谓“全才”,就是一个人表现出多种兴趣,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学习范围涵盖众多传统意义上不同领域的学问。许多艺术家在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创造出全新的完美作品,在其他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作为人本身同样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当中有的人除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之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有精深研究。以达·芬奇为例,他既是画家,又是解剖学的奠基人,研究兴趣涉及人体骨骼、肌肉、组织等,而这些部位当时通常被专业外科医生所忽略。他在论述为什么有必要采用图像表现的新方法时,列出理想解剖者的必备条件,指出在令人恐怖的尸体面前,他应当胃口大开、意志坚定、无所畏惧,同时还应当有能力计算肌肉的运动,能够速写、画图以及熟练运用透视法。我们从中可见达·芬奇本人作为一名“全才”所具备的各种才能。
在心智学术方面,在意大利,同样涌现出真正出类拔萃的“全才”。但丁、马基雅维里便是典型例子。但丁是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在造型艺术上也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马基雅维里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为“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尽管布克哈特声称这类“全才”为意大利所独有,但是英国人菲利普·锡德尼(SirPhilipSidney,1554—1586)等人的出现无疑使人有理由修正其论断。锡德尼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写下的《为诗辩护》既是一种新教诗学,又是一份人文主义宣言,不仅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划时代的足迹,而且在政治、哲学乃至在宗教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不同学科各种思想观点荟萃的著作。
在学科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全才”得以在心智上彼此激荡,相互启发。不同学科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团体,他们往往从其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譬如,语文学家、古文物研究家威利巴尔德·波科海姆(WillibaldPirckheimer,1470—1530)对数学有精深的研究,在他的启发之下,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开始研究阿基米德几何学,而丢勒的几何com学论文又被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引用。再如,医学领域的天才奇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Fracastoro,1478—1553)是天文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和出众的诗人,他对人的大脑及其思维过程有着独到的研究,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关于诗人创作过程的思考,就特别得益于他对人的大脑的分析。
“全才”的出现为学术大发展提供了契机,最重要的标识就是有意识的创新活动。在学科大融合局面形成之前,中世纪的各种学问都被局限在特定的边界之内,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它们似乎已经达到顶峰,取得新进步的可能性堪称渺茫。学科大融合及“全才”的出现使得改变这一局面成为可能,英国卓越的“全才”弗朗西斯·培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指出世界不会因人的理解有限而缩小范围,人应当使自己的理解扩大和开放,直至拥抱整个世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不再像中了邪魔的人那样,被局限在小圆圈中不停地跳舞,我们的航程和赛道将和世界罗盘一样宽广”。培根声称人类所有的学问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所关注的是把知识拓展到新的领域。在面对中世纪学术停滞的局面时,他不是谴责过去,不是查找前人的不足。他的哲学不是“修正”(renovation),而是“创新”(innovation)。在他看来,学术的进步不在于“灌输”某种已有的学说,也不在于“延续”传统,这两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都不是进步。培根把“灌输”和“延续”视为“培植”(cultivation),而不是一种“发现”(discovery),提出学术的进步需要新的出发点、新的学术兴趣、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从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中,诞生了现代科学,培根也被当之无愧地称为“现代科学之父”。
综上可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学科大融合的思想来源,在新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全才”,他们突破了原有的边界,将人类学问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何伟文 (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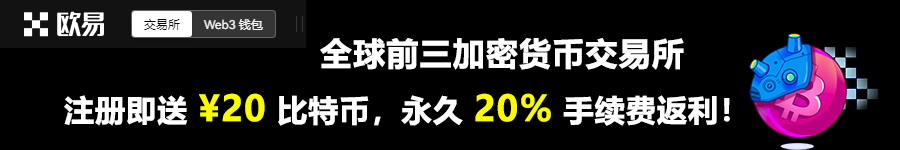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