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代州头条号是的山西代县本地自媒体号,致力于为山西的父老乡亲提供热点的资讯,搞笑的短视频,介绍山西的美食美景。挖掘山西的文化。欢迎大家关注惠代州头条号,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探讨的文章很多。但仅用抽象的概念去表述它,给人的印象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非模糊,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人,深晓其中三昧,般人则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我们还是从具象入手,从器物层面入手谈谈吧。
李汉荣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中医的一知半解”,我们摘抄几段:人对气味的记忆,是非常深刻和持久的,西药房的气味是化学的,工业的,是冲动的和暴力的,甚至是威慑的,那种气味让你感到理性和技术正向你包抄过来,它不与你商量,它说一不二,它要进入你的身体,要征服和修改你的命运,那里的药物都有商标,有规格,有着规范的造型,它们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化工产品。你再看那里的器具、针头、镊子、手术刀,都是些武器,随时要向病魔反击,还有听诊器,它有点像窃听器,窃听病魔的行踪。外科医生走上手术台,活象一个披挂上阵的将军,护士、助手那不就是他的战通讯员和作战参谋长?
中药房的气味是草木的、农业的、平和的和亲切的,甚至让你感到祖父身上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许多草本的、木本的药物混合成又苦涩又芳香又朴素又高贵的温暖气息。它是渗透的,而非进攻性的,是商量的,徐徐弥漫的,而非断然的,气势汹汹的。它的气息是这般温暖宽广,父性的刚勇母性的仁慈交融成这气息,山的充实水的空灵,交融成这气息,天的理性地的感性交融成这气以上这节文字的小标题是:“中药房”。下面一节的小标题是“中医大夫”。前一节说物,后一节说人;前一节说药房,说医院,后一节说医生,医理,特说中医大夫。
中医大夫不像医生,他是天文学家。他望着我的脸说:“你气色不好。”这不正是古代的占星士(那时的天文学家)望着天空在说:“星象呈凶兆”么?他又补充了句,“脸上有阴气”,他眉头微微皱起来了,好像是天文学家在太阳系附近发现了一个大黑洞。这位医生和蔼地笑了一下,轻声说:“没关系,吃副药会好的”,浮云遮月,只是彼此打了一个照面。他是水利学家。他拉起我的手,开始切脉,他在观察我身体里江河湖海的水情。脉有些滑,他说,“这不就是说河水快断流了,只有些残水勉强敷衍着河床?”
他又说,“脉有些滞涩,这当然是说该清淤了。”他是哲学家。多数时间里他很少说话,他在“格物致知”,他在沉思。一个个病体就是他哲学思考的对象。他以天地为师探求人体运化的原理。他仰观天文,平视人体,俯察地理。在天地的大洪流里,人该怎样寄存这小小一滴?他说:“天地与我同源,万物与我并生。人体者,微观之天体;天体者,宏观之人体。”阴阳、虚实、表里、寒热、风火、盈虚…他用这一对对概念描绘人体。
这是李先生的一篇散文,一篇文学作品,却可以说是一篇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明文,论证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它的确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要害,以中西医之比较来凸显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状态是什么样,我们已不得而知所见的仅是一麟半爪。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下子百家齐鸣,百花盛开,灿烂绚丽,就如节日的烟花,爆响空际,已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了。
以后历经两汉的儒学独尊,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昌盛,隋唐的佛学渐强,两宋的理学兴隆,再经元明清的融汰陶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不绝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传承不绝的传统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典册、概念、词语:一方面是人的生活样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思维特点。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后者又是前者的内核。这载体又不是消极传述,而是积极地影响,甚至起造就后者的作用。两者互为因果,在时间之流中相互作用,一体前行。
但二者之间时有超前或滞后的现象发生。前者犹如录音带,后者犹如歌声音源。前者具有静态性、符号性,后者具有流变性、无形性。录音者有时未能紧跟歌唱者,造成漏录;或者是某一歌唱者有超前性唱法被录了下来,而后来的演唱者则达不到那个水平,造成二者不能同步的现象。当然这二者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绝非如此简单,如此匕机械。文化之流就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前进,终于造就了特有的中国文化传
而这中医中药文化正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典型的体现。类似的事例俯拾即是,因为它们是由同一棵树结出的果。
我见过农村木匠牮房子。房屋的一根柱子有问题了,要换掉。房子是老式的,已多年,屋顶覆以筒瓦与板瓦两层,加上很厚的泥灰及椽檩等物,重量可想而知。要换柱子必须将房子撑起来,让柱子减去负荷,还得让出一定的活动空间能够操作,能够将相交接的榫卯脱开来,再插进新换的柱头。弄不好,柱子不能卸荷,房子却倾斜或坍塌了。但木匠则成竹在胸,不像我想得那么复杂。只见他用一条长厚板子,在板头下垫一截圆木,板头上顶一根直木,撑住与柱子相连的柁(大梁)颈,只用两个人在板子的另一头徐徐下压,屋顶便升高了。
这分明是利用杠杆原理,但木匠却说不出道理来,就这土办法,反正是行之有效,达成目的。
不探究抽象的物理数学道理,凭经验,就地取材,简单、实用、有效。我想,如果用洋办法,当然得用台起重机,至少得用一个千斤顶。而这工匠却什么也不用。这跟前面那个中医大夫的作为不是如出一辙吗?伸出手来把一下脉,伸出舌头来看一下舌苔,提笔开一副中药,完事。没有任何设备,顶多只有一根银针,将十指放放血而已。西医呢,刀子、镊子、听诊器应有尽有,还得建一个医院,置办CT机、X射线机,简直像一个工厂、一个兵站。
我们再比较几件中西乐器。差别最明显的是管乐器。中国笛子只短短一段竹子,开几个孔即成,而西方乐器中的短笛则不这么简单,它增加了按键;至于长笛就更为复杂。再看中国箫,也跟笛大同小异,只是竹管长了点,是直吹,声音沉稳,幽静;而西方的巴松(又名大管)则增加了S形吹管,还有别的许多零件。
在簧哨乐器中,管子与笙是代表。中国管子也是一截竹子开几个孔,它比笛子更短小,只是增中了一个哨咀,此外什么都没有,让艺人吹起来真是如泣如诉;而西洋乐器中的萨克斯管则复杂多了,上面密密麻麻加了许多附件。中国笙算是簧乐器了,可跟西洋乐器的手风琴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乐器
中国弦乐器的代表当数二胡或京胡、板胡之类了,跟西洋弦乐弦的主角大、小提琴比,同样是差别明显,其繁简程度同样是一目了然。至于钢琴,这是西洋乐器之王了,那复杂的构造直如一架精密的机器。
但是无庸讳言,中国乐器要想发出准确的音来全凭演奏者的丰富经验与纯熟技巧,而西洋乐器则精准得多,简捷得多,只要按下这个按键就会发出这个音来;而更有一些音响效果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
但是,我们喜欢听的仍然是二胡独奏的《二泉映月》,广东音乐《旱天雷》及其他《平沙落雁》、《春江花月夜》、《百鸟朝凤》、《渔歌唱晚》之类。而西洋的什么交响乐,协奏曲,甚至是名家名曲,如施特劳斯的《蓝色多脑河舞曲》、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肖邦的《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等,对不起,欣赏不了。
西洋乐器
中国人缺乏“音乐的耳朵”,乐感不强吗?绝对不是。我们二三千年前的祖先就曾以音乐作为教化的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乐。《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史记乐书》)。
古人能从音乐的旋律中听出国运的盛衰。《列子·汤问》载有一则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我我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中国人若没有鉴赏音乐的耳朵,能达此境界吗?类似的关于音乐的记载,在古籍中不乏其例,韩娥的歌声,司马相如的《凤求凰》、阮籍的《酒狂》,嵇康的许多琴曲,其音乐效果都是生动感人,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没有品鉴音响效应的能力焉能如此!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习惯爱好,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判断标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食粮,这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再看戏剧,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全有了它既是一个普通家庭,也是县太爷审案的公堂,还是万岁爷的龙廷大殿。演员往桌子上面一站,就是上了城楼,登上山峰。两面画着东轮的旗子,演员站在两旗子之间,就是坐了车。将一根带穗子的细棍子一扬,就是骑了马。四个演员在台上走走过场,就是千军万马。一个满脸涂了白油彩的演员一登场,人们就知道这不是好人,“白脸奸臣”已经成了评价人格的日常用语。这种高度象征化、符号化的方式,西方戏剧是这样的吗?绝不。
你随便拿一件物事跟西方世界的同类物事比较一下,都会发现二者的差异,都会悟出中国不论什么物品、什么艺术、什么作为,都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的马车与西欧的马车比,中国的毛笔与西方的钢笔比,中国的折扇与西方扇凉工具比,中医用的针炙的银针与西方的注射针管比,中国的寺庙与西方的教堂比,中国的传统舞蹈与西方的巴蕾比,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方的油画比,倪云林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比,中国的仕女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比,哪一样不是充满中国的鲜明特色而不同于西方?更典型的是中国人从出生至死亡,每天使用、一生不离的吃饭用具——筷子。
樊浩教授讲了一个故事,说深谙中国文化、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一个外国专家,有人问他中国人怎样使用那两根筷子吃饭,他不屑思考,脱口而出:“一只手拿一根呀!”这个“中国通”还是“不通”,他的思维逻辑依旧是西方的。
这就是文化,它深入各个角落,你的举手一抬足,都脱不开它,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死硬不变。但它的改变是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
(作者介绍:崔焕奎,代县东关人,学者退休教师)
标签: 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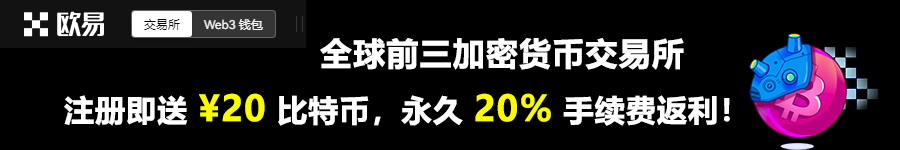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