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还有两三天的工期,做完便可以结算了工资辞职了。玉山上了一天班,便休息两天,一来陪我到处走走,二来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常州是个干净整洁的城市,我们有时坐公交,有时走路,我不觉成了一个闲散的人。在下了班的夜晚,四海聚来的打工仔们,在广场的空地上,放上音乐,跳起街舞,围观的男孩女孩们齐声欢呼。这似乎也并非出于热爱,无非是在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寻找一丝存在。就像谈恋爱,又有多少出于爱情,无非是闲来无聊,相互慰藉罢了。就像打架,棍棒打在头上,流出血来,打人者与被打者才能和颜悦色,手搭着肩,称兄道弟起来。
我在玉山的职工宿舍住了几日,便来了新的员工,没有多余的空床,我便说到“我晚上去网吧睡吧。”
“我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你在宿舍就行。”
玉山执意要去,我们便在网吧包夜,睡在网吧的沙发泰国小乘情降上。
玉山问我在查看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看看有没有机会拿个学历。
“成人高考吗?”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读个高职,学点技术也行。”
“学什么好?”
“学什么好……”玉山双手卡在一起,背过去拖住后仰的脑袋,仰面朝上看着屋顶,喃喃道:“学什么出来也不好找活,真没什么好学的。”
“唉,你知道荣杰,在北京学的会计,还是计算机,也没什么用。现在在南通跟她姐做服装呢,还有四件套,踩缝纫机,哈哈。”
“还有马蓉蓉,学的韩语,也回老家了,白花钱。”
墓地情降一定会成功“职高技校,给钱就能上,其实出来能干嘛呢。”
“上大学是没机会了。”玉山慢悠悠的说着。脑袋放平枕在交叉的双手上。
玉山在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位来自皖南的姑娘,彼此印象不错。在夜晚闲暇之余,两人通话良久,说着一些你侬我侬,暧昧的情话。不觉中,我在草木掩映的光影阑珊里无聊踱步了一个小时。青春男女间的情意绵绵总是能让人忘记时间。我不觉间又起了奢望与幻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那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次日,玉山约皖姑娘出去游玩,顺带我一同前往。那天阳光温暖,我们到达指定地点,皖姑娘也刚刚好到。皖姑娘穿着整洁干练,又有徽派山水滋养出的水灵美丽。玉山是有心的,皖姑娘是有心的。两人见面彼此欢喜,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不喜欢一个人也是伪装不来的。
玉山简单向我们介绍彼此,我们互相问好。恰逢其时道路的转角处追上来一个黑胖子,手里掕着满满一兜零食。
玉山问到“谁啊”
“我们厂一个黑胖子,非得跟着我,邀我去划船,烦死了”说着瞟去厌烦的目光。
黑胖子赶上前来“不是说约你去划船吗,这是你朋友?”
“谁答应跟你去划船了?”
“今天天气不错,正好咱们一起去。”
死皮赖脸能赢得爱情吗,我想不会吧,若果真如此,月上柳梢头时,还约吗,约出来岂不是玷污了月色与春柳精心营造的美的氛围。
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坐公交来到公园,散步,划船,登高眺望满园的景色,胖子始终不肯放弃与皖姑娘并肩同行的位置。南方的四季不甚分明,11月份也没有秋天的萧索,湖水温暖的柔波上,阳光起伏闪烁。下午三四点迎面吹来的风略有些凉意,我们互相作别,黑胖子与皖姑娘同行回厂,我与玉山也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我们坐车返回南通,我背着松垮破旧的背包,像一个落魄的流浪者。玉山的父亲讲起话来总带着一副通透且达观的笑容,漏风的牙齿挡不住他洪亮的嗓门,
“怎么,常州那边工作不好找啊。”
“嘿,有想去的厂子,人家还看不上我们。”玉山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平静与豁达。
生活并非是逆来顺受,或奋勇反抗,生活的风吹到哪,雨淋到哪,我便笑着在哪里发芽生长,这是父传子承的生活态度,而非浅薄的“随遇而安”。
“在你小叔这干吧。”
我则有些难堪和迷茫了,再次住进那间潮湿的小屋。玉山告诉我说他小叔的厂里暂时不缺人。“没事,我帮你找,这边厂子多的是。”
第二天玉山便带我在周边的村子找活干,还有久未见面的荣洁。我们即是同学又是同村,彼此也比较熟悉。荣洁在当年比较火的北大某鸟学了三年会计,终究没有用武之地,便南下投奔姐姐,姐夫。
寻找一天终究无果,玉山说“我有朋友在杭州某厂,可去试试。”
我说“好”
“滚吧你们两个,都快年底了,在这找个活干得了,还瞎跑。”
“还有你,玉山,净出馊主意。”
我们被荣洁训斥的无话可讲。
“我让我姐夫,我华哥给德敬找,笨死你们两个得了。”
荣洁性格十二分开朗,说话直来直去。
我们一直认为,她的发音器官是不经过大脑支配,而自己做主的。说话如此,大笑也如此。
我隐约察觉到玉山二婶的不满,大概是玉山帮我找工作,我还挑三拣四之类的。有大约嫌弃我在她这的两天白吃白住。
玉山的二婶是个村里有名的二婶,“精明,不吃亏。”
在第三天还没有合适的工作,我便在小叔的车间帮忙,
“婶儿,我来打包。”
“没事,没事,来,我教你。活倒是不累,就是靠的时间长。”
一个下午我不住脚的忙活打包,喂羊毛,收拾些零散的活。
玉山父亲走过来问到“脚伤好了吗,还疼吗,这活就是脏。”说着结果我手里的木扠,将羊毛填进机器里。
我说“时间长了还是会疼,能坚持。”
许久没有体力劳动,干了一下午,便觉得胳膊酸痛。
晚饭时间,机器停下来休息一个小时,玉山的二婶主动招呼我洗手吃饭,与以往僵硬而铁青色的脸不同,竟泛起活泼的笑容,这顿饭我自然吃的体面些。
我的内向与愚痴,竟也会有幸被生活指点,并牢记在心。
所幸我在同乡的帮助下在另一家加工作坊里找到了工作。南通市的石桥镇坐落着大大小小的生产车间,外来谋生闯荡者居多,那几年经济还景气,凡是投资办厂的都能挣到钱。有创业者便有打工者,外来开厂老板,一般都会在老家招募愿意外出务工的相邻或亲戚。人手不足时,回去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招人,但总归用自己熟悉的人放心。
机器24小时在转动,四个人为一条流水线作业,八个人每12小时一轮班。夜班和白班每周轮换一次。我第一周被安排到了白班,跟我同班有两个与我年龄相当的女生,一个是我的同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走了形的肥胖身躯干起活来便显出一丝笨拙,另一个女生是个河南人,大概是从人力市场找来的,女人大概刚结婚不久,小两口从河南农村外出谋生。河南女生扎着松散的辫子,面容俊秀,眼神里透着北方女子的古朴与坚毅。这种眼神我在母亲的眼睛里看见过,在妹妹的眼睛里看见过,在千千万万个如母亲一样的女人眼睛里看见过。另一个是个矮个子的男人,体型消瘦,穿在身上的衣服空空荡荡的,看不出身体的轮廓,男子来自安徽,据说已经36岁了,还没有结婚。我想这大概是真的,此人完全没有一个成年男人的成熟迹象,待人接物都表现的幼稚。
整套设备的程序并不复杂,我在一端将羊毛或者纤维喂进机器张开的嘴里,机器转动,将扎堆的羊毛铺平,履带载着前行,再将其轧实,切成设计好的尺寸大小。两个女人将轻薄的切片叠好,小个子男人负责将其装进薄薄的塑料袋里,二十或三十一包,挤出塑料袋里的空气,压实,封口,靠墙叠放。有时我们两个互换,他来喂毛,我去封包。
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工时,中午吃饭,机器休息一个小时。我盯着机器张开的嘴,不停的用木扠续料。才半天的时间便体楚臂乏,胳膊腿酸痛起来。伤腿也僵硬疼痛,我便瘸着腿干活了。坚持完一天的活。天色已昏暗下来,去车间对面的房间里吃过晚饭,疲惫的躺在床上,不想动弹。
厂房的对面是一排简陋的屋子,用来住人,每间屋子能放两张单人床。
玉山干完一天的活还是精力十足,便来看我,我从床上爬起来,已经没有心情过多的交谈。玉山让我早点休息,又去溜达去找荣洁了。我偏偏又犯了失眠,反复睡不着,玉山把他的手机给我,让我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我大概是对目前的处境感到焦虑和惶惑。自那时起我成了失眠惯犯。
“酒能解乏,走,咱爷俩喝一杯。”又是一天的劳作后,玉山的父亲拉我去家里吃晚饭,六块钱一瓶的白酒,玉山的父亲给我和玉山各倒上一杯。自己一口酒一口菜喝的有滋有味。每咽下一口白酒,他都会紧咂着嘴,眉头一缩,随之舒展开来。我也端起酒杯,饮进一小口,纯纯的酒精火辣辣的灼烧着咽喉和食管,呛得我咳嗽起来。
“赶紧吃口菜。”
我索性敞开了,又灌了三四杯。
“行,德敬,别喝了,差不多了。”
玉山给我递过一碗白水。
我昏昏沉沉,踉跄走回宿舍,躺在床上更难受起来,胃里火烧火燎,且头阵阵作痛。整个晚上也没睡好觉。半睡半醒间,天已经蒙蒙亮了。吃过早饭就开工了,头痛依然脉冲式袭来,带动右眼皮不自觉抖动一下。我想酒能解乏,酒精加水就有点不讲究了。
南方的秋雨倒像夏雨的尾巴,没有征兆的突如其来,打湿泥土后又戛然而止。似乎没有秋风的助势,也就没有了连绵不绝的勇气。南方的秋天少了肃杀与萧索的情绪。没有了情绪的秋天也便不像秋天了。
天津在一场场秋雨过后,天气一天天凉了起来,裘小昌走出车间。仲秋夜晚的凉意,让他不觉双手交叉抱紧肩膀,一件运动外套紧紧裹着单薄的线衣,夜风吹透衣服,洒在肌肤上像一汪水里的月光。他该为自己添加些衣物了。
小昌走出厂门,晚上八点左右的城市灯火通明,路灯投下温暖的光。小昌走过两个街口,又拐进一截宽阔的街巷。这里有廉价的快餐店,小吃店,服装店,超市,下了班的男男女女或来觅食填腹,或来买着生活用品,熙熙攘攘。在街道的一侧有一家物华超市,拉开长条的横幅,写着各种优惠的标语。超市的旁边是服装店,门面上写着荣记服饰的字样,门店外悬挂的灯箱招牌,已经退了许多色彩,没有了最初的鲜亮。走进室内,内墙和地面干净整洁,在灯光的照射下室内环境给人温馨感,且衣服摆设井井有序。
店长是个四十出头的体态微胖的女性,留着短发,发梢染成亚麻色。老板娘叫李亚军,是本地人,此时正在招待进进出出的顾客。叫小昌推门进去,老板娘热情招呼到“来了,兄弟,看看要点啥,外套还是毛衣。”
“我看看”
“都是刚进的新款,有相中的可以试一下。”
“小蕊,来一下。”老板娘李亚军叫到。
在靠近试衣间的角落里整理衣物的张小蕊走了出来。女孩个子不高,衣着干净利索,扎起的头发顺在米黄色的外衣上。女孩笑嘻嘻走过来,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眉宇间透露着喜悦的神情。
“哥,要点啥,可以试穿,天凉了,买两件毛衣,买两件打八折。”
“好的,我看看”
进进出出的顾客多了起来,大多是附近厂里打工的年轻人,张小蕊一边伴着小昌,一边招呼着其他顾客。裘小昌挑了两件毛衣,大约合身,也无需试穿,付过钱推门走了回去。
落叶在晚风里打着漩涡,聚集成堆,又忽而被吹散开来,在马路上漫无目地游荡。
小昌来天津已经一年多,除了周天,每晚有固定的两个小时的加班。算下来一个月能有3000多的收入。小昌除了必要的花费,工资都存在卡上。小昌明白现在攒下的每一分钱将来都该用在刀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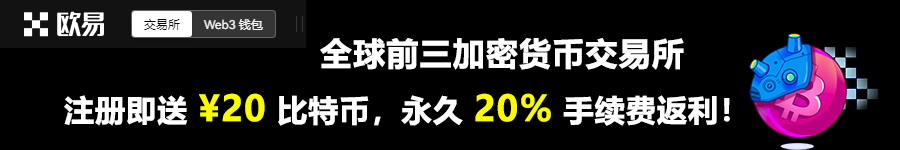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