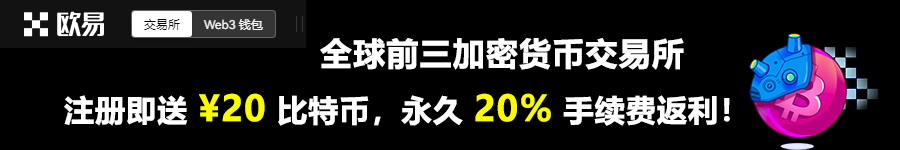日本人玉村丰男的《全球蔬菜纪行》里写新疆的塔吉克、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共有的美食——抓饭,“在中国的抓饭里,番茄、辣椒、洋葱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胡萝卜则不那么受重视……”看到这里,我竟要替我故乡的众民族弟兄姊妹们勃然大怒,甚至想仿照《查令十字街84号》的女主角海莲看到错误百出的书那样,要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用来包书——幸好我没有书需要包。玉村丰男所说的“中国的抓饭”是塔吉克人的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蔬菜是胡萝卜和洋葱,见不着番茄、辣椒的身影。如果说有关系,也是后来人们因抓饭油较多,而常配一盘由番茄、辣椒、洋葱组成的名叫“皮辣红”的凉拌菜。但玉村丰男后来也在文中补充:“随着地域的变化,抓饭里渐渐出现了胡萝卜,人们甚至还要执着于红色的胡萝卜好还是黄色的好。”我就渐渐原谅了他。
插图:白芳圆
如果恰逢3月中旬塔吉克族过肖贡巴哈尔节,一定要进入这个迎接春天的节日,行走在各个村子的奔走祝福声中,接受主人撒在客人肩膀上表示祝福的面粉。这时候在塔吉克人的房间里,天顶罩下来的光都有春天的生气。男主人盘腿坐在被挂毯、坐毯、枕头、被子包围的如花似锦中,用随身带着的刀子熟练地把羊肉削成一块一块,按照一定秩序分给众人……最后一道“菜”当仁不让是米粒通体透明、油黄流香的抓饭。
“皮牙子在蔬菜中趾高气扬,胡萝卜在茄子面前炫耀自己的堂皇。”生活在17、18世纪的巡游诗人则勒力在《萨克诗简》中写到这句时,想到的大约也是手抓饭,否则这两样做手抓饭的菜蔬在他的诗里,怎么会如此气宇轩昂。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但在做好的抓饭中,洋葱却完全不见了踪影——在羊肉、大米、胡萝卜、油的“知遇之恩”中,洋葱被融化殆尽在抓饭里,唯余灵魂的风味在抓饭的晶亮里顾盼生辉,胡萝卜的黄则在抓饭里流动成凡·高的星空。
说起抓饭必不可少的胡萝卜,我一度很疑惑:不是应该叫黄萝卜吗?缺少了黄萝卜,怎称得上正宗的抓饭?黄萝卜在国内的种植地域并不多,新疆算是最重要的产区之一。尤其在南疆地区,抓饭中黄、红两色胡萝卜的配比,前者要稍高一些。黄色的水分更充足,红色的口感更加香甜,两种颜色的胡萝卜成就了抓饭鲜亮的色彩。
胡萝卜既然前头冠以“胡”字,即可纳入“归雁入胡天”的传奇。它的原产地是近东和中亚地区,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相邻的阿富汗,是紫色胡萝卜(现代品种的原始祖先)最早的演化中心,栽培历史顶级墓地情降在2000年以上。胡萝卜喜欢冷凉的气候,需要较大的温差以利于肉质根的建构与形成,同时保证较高的胡萝卜素、茄红素的含量。新疆阿姨来海南时说:“这地方,什么菜的味道都比新疆淡几分,皮牙子、胡萝卜都没味了。”我倒是没感觉出来,大概是我离开新疆太久,已不知洋葱和胡萝卜真味。但细想,从植物生长环境特性来说,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摄影:王毅楠
不同地区植物的分布是有差异的。春秋时代《晏子使楚》就提到植物的分布问题:晏子到楚国游说结盟事宜,楚国人看不起矮小的晏子,想要羞辱他。在楚国的酒宴上,两个士兵押了犯人进来。楚王问:“什么人?”士兵答:“齐国人,小偷。”楚王转头问晏子:“齐国人是否很擅长偷盗啊?”晏子离席答:“橘生长在淮南就是橘,到淮北就变成了枳,为什么?水土不同啊。老百姓在齐国不偷盗,跑到楚国就变成了贼,难道不是楚国水土养育的结果吗?”当然,故事里的南橘北枳,显示的是晏子化羞辱为反击的智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植物划分带的问题。
植物的分布除了地质、历史等因素以外,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每种植物的需热量和忍受极端温度的能力是不同的。地球表面热量的分布很不均匀,所以在不同的气温带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不同的植物种类。在我国,秦岭—淮河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它的北面是暖温带,南面则是亚热带。这条界线两侧的自然景观差异很大,植物种类差别也很大。此外,气温及积温也会导致植物的差异。
比如胡萝卜,虽然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但滋味却不同。胡萝卜开花结果时,会尽量多地积累养料在果实中,可如果温度超过一定限度,光合作用就会减弱,呼吸作用加强。这样一来,胡萝卜的生长就受到限制,甚至还要消耗已积累的养料。于是,新疆阿姨来到海南,嗔怪这里的洋葱不够趾高气扬也就不奇怪了。
插图:白芳圆
所以还是到塔什库尔干去遇见胡萝卜吧,如果没有人给你从田野里直接拔鲜亮的胡萝卜吃,那就吃抓饭吧。如果遇不到塔吉克族的肖贡巴哈尔节,就走进塔什库尔干县的饭馆里去遇见金黄流油的抓饭吧。
高原的生活造就了抓饭,塔吉克人的个性和生活样式造就了它的味道。在塔吉克人的抓饭里,高原的风、劈面而来的雪峰、花团锦簇的毡房、柴火烧热的炉灶……它们和食材合在一起,构成了塔吉克人的抓饭。
文字根据线上传播方式对原作有部分删改。
撰文:安歌。内容来自:《地道风物·帕米尔之心》